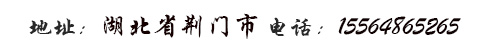60后,你还记得文革那些岁月吗钟晓杂谈
|
北京什么医院治疗白癜风 https://yyk.39.net/hospital/89ac7_map.html 青少年时期正值文革十年动乱。 那个时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既没有歌厅、舞厅,更没有电视、电脑,就连露天电影也难得一见。好不容易碰到放映露天电影,也往往是老掉牙的片子,不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就是样板戏《杜鹃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再不就是译制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第八个铜像》等,还经常“白毛女”(那个时候我们管满心希望地到另一个村子去看露天电影,结果失望而归,叫做“白毛女”,即“白跑路”)。就算是这样,我也是乐此不疲。只要一听说什么地方放电影,就会早早地吃了晚饭,邀约一班狐朋狗友匆匆赶去抢滩占位。因为这是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呀,岂能错过?在那样的背景下,唯一可以作为经常性消遣的就只剩下书了。可是历经文革劫难,要找书,特别是自己感兴趣的书还真不容易呢。于是乎,我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书来看,有向别人借的,有拿书跟别人换的,有拿东西跟别人换的,还有从人家家里顺手牵羊拿的,什么情况都有。而且什么书都看,只要是书就行。什么文革前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文”(语文)教材呀,什么《第二次握手》《连心锁》等手抄本呀,都是那个时候看的。更为难得的是,我还看了直排版的《西游记》、《水浒》(七十一回本)、《绘画三门街》等,阅读古文和识繁体字的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那时看书也不拘什么形式和时间:坐着看,躺着也看;吃饭的时候看,上厕所的时候也看;天一亮就看,过了半夜还看。因为看书入迷,村里的人给我起了两个绰号:“鸡毛眼”(意思是看书看得眼睛都近视了。那个时候,近视眼是极稀罕的)、“书呆子”。可我却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照看不误。在学校里读书时,遇到自己不感兴趣、不喜欢听的课,我就看课外书。当然是偷偷摸摸地看,上面盖着一本教科书,下面藏着一本课外书。也曾多次被老师逮住,自然就免不了要上上“政治课”。记得,最多的一次竟被班主任老师数落了两个多小时。可过后,还是贼心不改。到了十六七岁,身心已基本发育成熟。虽然那时思想禁锢甚严,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直至高中,男女生之间也很少说话,一说话还会脸红呢,更不用说牵手搭背了。但内心里难免也会春心萌动、情窦初开。所以,当时,最爱看的自然就是书中那些谈情说爱的情节了。拿到书后,首先是快速翻看有没有这些情节。一看到这些情节就会激动不已,心跳加剧,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脸红。而且对于这些情节往往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咀嚼,形诸画面,进行联想,大有百看不厌的味道。有些片段竟至于烂熟于心,直到现在还能很流畅地背出来。譬如《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一章:“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崔生与张莺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初次借到《红楼梦》,如获至宝,大喜过望。由于归还日期很紧,不得已我只好“一灯如豆”,就着煤油灯(那时家里穷,还没有装上电灯)连夜将它看完。一夜鏖战,两眼通红。一声鸡啼,唤出太阳。天亮了,揉揉朦胧醉眼,伸伸酸麻懒腰,我还得匆匆赶去上学。因为夜读耗尽了瓶里的煤油,第二天还被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我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沉浸在宝黛的爱情故事中久久难以自拔。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eguxijiaerbaa.com/xjebjd/11499.html
- 上一篇文章: 俄乌冲突下欧洲之殇特稿米珠薪桂居不易
- 下一篇文章: 东方快车之巡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