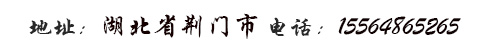马尔科姆middot劳里在火山下
|
马尔科姆·劳里(MalcolmLowry,-):英国小说家、诗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于年出版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在火山下》(UndertheVolcano),位列“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ModernLibraryBestNovels)“第11位。劳里于年6月死于与妻子一同租下的村舍,可能的死因包括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巴比妥类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本文译自小说第一章的开头部分。 小说讲述了墨西哥小城瓜乌纳瓦克(Quauhnahuac)的英国领事杰弗里·菲尔明(GeoffreyFirmin)在年11月1日死人节(DíadeMuertos)上发生的故事。全书叙事基于现实的地理位置,但有时会进行修改,此外还充满复杂的象征与隐喻,因此译文提供了大量注释,主要参考TheMalcolmLowryProject(链接见“阅读原文”)。 全书的最后一页是一组西班牙语标语: ?LEGUSTAESTEJARDíNQUEESSUYO??EVITEQUESUSHIJOSLODESTRUYAN!您喜欢这个花园吗您的花园?别让您的孩子把它毁了!这是这条标语第三次出现。作者在手稿中表示此处应该采用正确的标点符号(前两行形成整句,而非分开的两个问句),企鹅出版社版标注有误,此处按照作者意图译出。第五章这条标语第一次出现时,菲尔明领事曾把它错误地翻译为:Youlikethisgarden?Whyisityours?Weevictthosewhodestroy!您喜欢这个花园吗?为什么它是您的?我们要放逐毁灭它的人!关于“花园”,作者在年小说法文版序中写道:“对我来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人们深陷其中的种种力量,迫使人面对自我时感到恐惧。它还讲述了人的堕落、悔恨、负担着过往的重负不停地为光明而斗争,以及他的命运。这是伊甸园的隐喻,它象征世界,而如今世界恐怕要拒绝我们,比我写作这本书时更甚。”本书原文掺杂了大量西班牙语和法语表达,均在括号内标注原文。此外,书中“比希尔医生”这一角色的英文并不标准,在译文中也有体现(详见注释9),恳请读者留意。 两条山脉大致上由北向南纵贯共和国,之间形成了一些山谷和高原。其中一道山谷由两座火山统领,俯瞰这山谷的是海拔一千八百米的瓜乌纳瓦克城。它的位置比北回归线还要往南,确切地说,是在北纬十九度线上,向西与太平洋的雷维亚希赫多群岛,或者更西面的夏威夷群岛最南端同一纬度;向东则有尤卡坦半岛大西洋海岸上的祖考克斯港,距离英属洪都拉斯边界不远,或者遥远东方的朱格诺之城,一座孟加拉湾沿岸的印度城市。城镇建在山丘上,城墙很高,街巷扭曲、破碎,道路曲折。一条笔直宽阔的美式公路从城北深入,却迷失在城区狭窄的街道中,只伸出一条羊肠小径。瓜乌纳瓦克有十八座教堂和五十七家酒馆(cantinas);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尔夫球场和不少于四百处游泳池,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山上的水不断倾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豪华酒店。森林俱乐部酒店位于城外一座更高一些的山丘上,离火车站不远。酒店建成时间远远早于主干道,四周花园和露台环绕,各个方向的视野都很开阔。它宛如一座宫殿,处处弥漫着某种凄凉的华美气息。酒店已经不再用作俱乐部了。甚至没有人会在酒吧里玩骰子喝酒。破产赌徒的幽魂在这里徘徊。似乎从来没有人在壮观的奥运会级游泳池里游过泳。跳板伫立着,空洞而哀伤。荒芜的回力球场杂草丛生。两片网球场地也只在赛季时才有人维护。面朝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死人节的落日,两个身着白色法兰绒的男人坐在俱乐部的主露台上喝茴芹酒(anís)。之前是在打网球,然后打了台球,两人的网球拍套着的防水罩被攥得起皱——医生的是三角形的,另一个是四边形的。球拍靠在前面的矮墙上。随着弯弯曲曲的队伍从酒店后侧山坡下的墓地靠近,凄婉的歌声也传到了两人的耳朵里。他们转身看向吊唁的人群,不一会儿就只能看见人们手上的蜡烛忧郁的光,在远处捆扎好的秸秆间绕行。阿图罗·比希尔医生把“猴牌”茴香酒瓶推向雅克·拉吕埃勒先生时,他正专注地向前倾着身子。在他们右下侧不远,巨大的红色夜空下,荒凉的游泳池散落在各处,流淌着血色,宛如满目幻景,那是小城的平和与温馨。从他们坐着的地方来看确实十分安静,只有像拉吕埃勒先生现在一样凝神静听,才可以听到遥远而模糊的声音——这声音与微弱的哀叹声和哀叹者的铃铛声不同,却又无法与之分离:歌唱、升调、降调和稳定的踩踏声——持续了一整天的节日(fiesta)的叫喊与轰响。拉吕埃勒先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茴芹酒(anís)。喝茴芹酒(anís)是因为能让他想起苦艾酒。他的脸颊透着深红,手放在酒瓶上轻微地发抖,标签上通体红润的小恶魔朝他挥舞着杈子。“我当时想劝他去醒醒酒(déalcoholisé)。”比希尔医生说。他磕磕绊绊地讲出法语词,又继续用回英语。“但是那天我自己状态也很差,从舞会出来了后,我在舞会上觉得痛苦,身体,真的。这样非常不好,因为我们医生都要活得像使徒才可以。你应该记得我们那一天还打了网球。反正,我在领事的花园里勘(看)到他后,我让了一个男孩下去问他是否愿意过来几分钟,敲我的门,最好他来,要不然就给我写张条子,如果喝酒还没有把他煞死(杀死)的话。”拉吕埃勒先生笑了。“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医生继续说,“对,我想也问问你,那天你是否在他的房子堪(看)到他了?”“你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在我那,阿图罗。”“噢,我知道,但是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实在是醉得厉害,完全喝醉了(perfectamenteborracho),在我看来,领事和我一样糟,”比希尔医生摇了摇头,“不仅身体会生病,以前叫‘灵魂’的部分也会生病。你的可怜朋友,他在这样没完的悲剧里,天啊,花这么多钱。”拉吕埃勒先生喝完了酒。他起身走向矮墙,两只手分别搁在两支网球拍上放松,凝视着下方和四周的景象:废弃的回力球场,围墙里长满了草;死气沉沉的网球场;酒店大道中央的喷泉离得很近,有个仙人掌农夫勒住了马在喝水。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男一女,在楼下的副阳台上打起了过时的乒乓球。仅仅一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现在看来却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有人可能会认为当下的种种恐惧会把那件事像一滴水一样吞没。但并不是这样。尽管悲剧正在变得不真实并逐渐失去意义,但是人们似乎还是可以回忆起过去的日子,那时个人的生活依然有价值,而不只是公告上的印刷错误。他点了一根香烟。在左侧,东北方向远处,东马德雷山脉谷地和梯田的另一头,两座火山清晰地耸入落日,那是波波卡特佩特和伊斯塔西瓦特尔。近一些的,大约十五公里远,比最大的山谷低一点的地方,他认出树林环抱的托马林村。树林里升起一缕淡淡的蓝烟,是有人为了获取木炭非法焚烧木材。在他面前,美国公路的另一边,遍布着田地和果园,一条小河流淌其中,与阿尔卡潘辛格路相伴。一座监狱的瞭望塔从河流与道路之间的树林中抬起,道路蔓延向远方,消失在紫色的山坡中,像是多雷的天堂。在城里,瓜乌纳瓦克仅有的一家电影院突兀地建在一面斜坡上,忽然亮起灯,闪灭,又亮了起来。“‘人不相爱就不能活下去(Nosepuedevivirsinamar)’,”拉吕埃勒先生说,“那种蠢话(estúpido)题在我家房子上。” 多雷为但丁《地狱》开篇作的插画,见注释5和注释12“哎,朋友(amigo),把脑子放空就好了。”比希尔医生在他身后说。“但是老兄(hombre),伊冯娜竟然回来了!我根本没法理解。她回来找他了!”拉吕埃勒先生回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特瓦坎矿泉水喝了下去,说:“祝我们健康又有钱(Saludypesetas)。”“还有挥霍的时间(Ytiempoparagastarlas)。”他的朋友回应道,似乎在想些什么。拉吕埃勒先生看着医生打着哈欠躺倒在蒸笼椅上,英俊的、英俊到不现实的、暗色的、沉着的墨西哥人的面庞,亲切的、深棕色的眼睛,天真的眼睛,那种能在特万特佩克见到的瓦哈卡孩童美丽而哀伤的眼睛(特万特佩克是女人干活而男人整天在河里洗澡的理想地点),纤长的小手和瘦弱的手腕,手背上却长着些许粗犷的黑色毛发。“我早就把脑子放空了,阿图罗。”他用英语说,精致而紧张的手指取下了嘴里的烟。他知道自己戴了太多戒指。“但是越放它越满。”拉吕埃勒先生发现自己的烟抽完了,就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茴芹酒(anís)。“不介意的话(conpermiso)……”比希尔医生瞬间从口袋里变出一个打着火的打火机,简直像是一开始就点燃了一样:他从自己身上扯出了火焰,仿佛拿打火机和点火是同一个动作。他给拉吕埃勒先生举着火。“你不会从来没有去过这里的教堂吗?那里接待有亲由(亲友)去世的人,”他突然问,“圣母会陪伴没有人陪的人。”拉吕埃勒先生摇了摇头。“没有人去那儿。只有没有人陪他们的人才去。”医生慢慢说。他收起打火机,灵巧地转过手腕,看了看手表。“我们走吧(allons-nous-en),”他又说,“我们走吧(vámonos)。”他笑着打哈欠,点了几下头,像是为了向前引身子,直到脑袋停在两手之间。随后起身,和拉吕埃勒先生一起站在矮墙边,深呼吸几口。“啊,但我喜欢现在这个时候,太阳落山,所有人都在唱歌,狗也在叫唤。”拉吕埃勒先生笑了。他们说话的时候,南方的天色变得粗野,仿佛要下起暴风雨。吊唁的队伍已经拐过了山丘。昏昏欲睡的秃鹫在高空顺风滑翔。“差不多八点半了,我要去电影院(cine)了,待一小时。”“行(bueno),那我们晚上再见,就在你知道的那个地方。别忘了,我还是不信你明天就要走了。”医生伸出手,拉吕埃勒先生紧握着,情意满满。“看看能不能晚上过来吧,要不然就记着,我一直都关照你的身体健康。”“回头见(hastalavista)。”“回头见(hastalavista)。”独自一人站在高速路旁,看着四年前最后驶过的道路,从洛杉矶出发的疯狂而美好的旅程,拉吕埃勒先生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马上就要走了。有关明日的思绪几乎吞没了一切。他停下来,没决定好走哪条路回家,过载的小巴士——开往托马林广场(TomalínZócalo)——晃晃悠悠地从他身边开过,向下驶入低谷(barranca),之后才爬升到瓜乌纳瓦克。今天晚上他不想朝这走。他穿过马路,走向车站。尽管不乘火车走,但是即将启程的、迫近的感觉还是涌上心头,他像个孩子一样避开转辙器,越过窄轨铁道。落日的余晖掠过远处筑堤草地上的油桶。站台沉睡着。铁道空荡荡,信号机臂板横起。几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真的会有火车停靠在这里,除了这样一块牌子:QUAUHNAHUAC 瓜乌纳瓦克注释本句逐词照抄了《文学摘要:世界地图册与地名词典》(TheLiteraryDigestAtlasoftheWorldandGazetteer)中描述墨西哥一章的原句,但是额外添加了“大致上(roughly)”一词。 瓜乌纳瓦克(Quauhnahuac):墨西哥城市,莫雷洛斯州首府,纳瓦特尔语意为“林木环绕之处”,一般按西班牙语称为“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作者特意使用纳瓦特语名而没有使用常用的“库埃纳瓦卡”,他曾解释说:“这本书里的瓜乌纳瓦克不是库埃纳瓦卡[……]” 祖考克斯(Tzucox)和雷维亚希赫多群岛(RevillagigedoIslands)分别是墨西哥领土在北纬十九度线上的东西两极。 朱格诺(Juggernaut):一些地区的印度教徒与佛教徒信仰“世界之王”贾格纳神(Jagannath),即毗湿奴的一种形态。孟加拉湾沿岸的布里市(Puri)每年会举办庆典,人们将贾格纳神的形象放置在华丽的大推车内,在布里市的两座寺庙间运输,运输的过程即是“朱格诺”,意为“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森林俱乐部酒店(HotelCasinodelaSelva):现实中建立于年,年开始仅用作酒店。对此,作者在给出版人乔纳森·凯普(JonathanCape)的信中写道:“Selva一词的意思是‘林木’,让人想到《地狱》的开篇。”《地狱》)(Inferno)是但丁《神曲》(LaDivinaCommedia)的第一部分,开篇是: Nelmezzodelcammindinostravitamiritrovaiperunaselvaoscuracheladirittaviaerasmarrita.在我们生活的中途我身处昏暗的森林,正路已不见踪影。死人节(DíadeMuertos/theDayoftheDead):通称“亡灵节”,此处按字面意思直译。墨西哥重要节日,在每年11月1日至2日举办,气氛热烈。“猴牌”茴芹酒(AnísdelMono):发源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省巴达洛纳市的著名茴芹酒品牌,标签上总是画着一只拿着酒瓶的猴子。西班牙语姓“比希尔(Vigil)”来源于拉丁语vigil,意思是醒着的、警戒的,也可以指守夜人。法语姓“拉吕埃勒(Laruelle)”字面上可拆分为名词组laruelle,意思是街巷,还可以指床与墙壁或另一张床之间的空隙。比希尔医生的英语不好,主要有几个问题:首先,为了突出比希尔医生的口音,作者在一些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的词缀上加了重音符`,写作-èd,表示医生受西班牙语习惯影响错误地重读了词缀的元音;其次是动词使用和形态错误(looked-saw,sended-sent,have-has,spend-spent);最后还有一些受到西班牙语习惯影响的语法和用词(physical,really:副词连用省略第一个副词词缀;ifnot:直接对应西语常用的sino,注意从后文中可以看出来医生只会使用ifnot这个表达;thinkto:对应常用的pensar——这些表达在英语中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相对来说在英语中并不常用)。译文尽量在保持文意通顺的前提下调整了一些语法和发音。托马林(Tomalín):作者虚构的村庄。阿尔卡潘辛格(Alcapancingo):或指阿卡潘钦格(Acapantzingo),库埃纳瓦卡周边地区。指法国插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Doré)为《失乐园》(ParadiseLost)画的插画。西班牙语中的常用祝酒辞。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eguxijiaerbaa.com/xjebjd/6522.html
- 上一篇文章: 去那神往的地方咖啡与玛雅文化的圣地下
- 下一篇文章: 今日头条云南16个地州市已经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