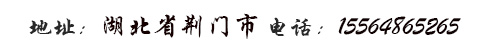吴晓筠商周时期铜镜的出现与使用
|
商周时期铜镜的出现与使用 吴晓筠 一、前言 目前所知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集中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它们非安阳地区出产、带有强烈草原文化特征等已是学界共识,但其来源为何,迄今仍争议不休。如下文所示,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或认为发现于甘肃、青海及内蒙古的齐家文化晚期铜镜是中国最早的铜镜,或认为新疆天山北路发现的铜镜才是商周铜镜的源头。另一方面,在大量的研究论著及图录中,过去关于中国铜镜的论述,经常将铜镜自齐家文化及商代晚期出现开始,历经两周秦汉,乃至于清代,视为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1]但若将安阳发现的几何纹镜(附录一:1~6)与西周时期尺寸偏小的素面镜(附录一:7~9、19、21、24)相比,如下文所提出的,两者之间可能没有承继发展关系。 今日考古发现已累积丰富的材料,亚洲内陆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因此,本文由西元前两千至一千纪考古学文化脉络出发,回顾过去相关研究、梳理现有考古资料,试图厘清铜镜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创制。 二、发现与研究 (一)早期铜镜资料的累积与中原铜镜起源的认识 因铜镜具有反射、光亮等特性,故而在古代文献中,经常被认为堪比日月,并赋予神话性格。如此神物的起源,便被比附为远古黄帝合日月之精华所创造,并为古代皇帝所相信。[2]这种认识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有所改变。 二十世纪初,随着考古学引进中国以及市场对古董需求而来的大量私掘,大量古代青铜镜出土,其中不乏一些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例子。例如瑞典安特生(JohanG.Andersson)便曾于一九三二年报导一面采集自内蒙古的重圈纹铜镜(附录二:51)。[3]后续于一九七○年代青海贵南尕马台铜镜[4]及甘肃广河齐家坪[5]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更被确认为中国最早的铜镜,起源问题便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中国铜镜起源问题的主要解释模式可分为中原本土起源与外来说两种。本土起源的说法多由古文献及中国青铜器的使用脉络出发,认为镜是由盛水的铜鉴衍生出来,[6]由阳燧发展而来,[7]或认为是源自多种具有反射效果的金属器。[8]李亨求依据风格分析及当时所知的考古学文化定年,认为是商人发明铜镜后北传至西伯利亚及朝鲜半岛。[9]但因近年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出土,中国境内及欧亚草原青铜及铁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定年分析有长足的发展,今日已鲜有学者强调中原本土起源说。早期外来说的主张主要由日本学者提出。自一九三○年代起,梅原末治、江上波夫等学者便已讨论中原所用铜镜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梅原末治认为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10]江上波夫提出绥远式青铜器的概念,并将之与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相连接。[11] 一九七六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四件几何纹镜(附录一:1~4),其中一面与安特生发现的铜镜几乎一致(附录一:2),更为草原说提供坚实的证据。[12]林沄在论述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时指出妇好墓铜镜与北方系青铜器之间的关系,极具启发性。[13]但学者通过妇好墓与中国西北及北方地带出土铜镜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原地区所见铜镜来自新疆天山北路[14]及来自齐家文化[15]等两种主要观点。近年随着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两面殷墟时期铜镜出土,北方地带做为铜镜自西北向中原传递的路径,也受到学者注意。[16] 随着欧亚草原考古资料的公布及翻译,一些学者也尝试跨越当代国界,将中原地区纳入更大的地理空间中的评估。在这些研究中,铜镜与刀、斧等工具一起成为探讨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互动的标志性器物。俄国考古学者ElenaE.Kuzmina自一九八○年代起便开始与美国学者合作,将俄国学者百年来对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发现及研究进行英文编译,成为研究俄国考古材料的重要参考。[17]在这些著述中,她反复提及商代晚期安阳地区的铜镜可追溯至欧亚草原分布广泛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更接近的来源则是经由新疆再传到商都所在的安阳。[18]胡博(LouisaG.Fitzgerald-Huber)就二里头遗址所见圆形铜片上的十字纹及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铜镜上的星芒纹,认为齐家文化与巴克特里亚及南土库曼地区所见陶器及铜饰件纹饰的相似性,并提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actria-MargianaArchaeologicalComplex(BMAC),c.-BCE)与齐家及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可能关系。[19]近年张莉延续胡博的观点,强调应跨越现代国界的研究素材限制,并论述铜镜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出现是受到中亚草原地区西元前第二千年纪早期的BMAC的影响,之后再经由北方草原地带以舶来品的形式进入中原。[20] 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学者中,以DianeM.O’Donoghue最为重要。他由商代晚期及西周时期铜镜的稀少性认为晚商、西周铜镜基本均为舶来品,并似对此类器物是否可称为镜子感到怀疑,因而在行文多处见到以「reflector(反射物)」及「mirror(镜)」称之。[21]白云翔由铸造技术出发,从新的角度论证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所见铜镜均非本地铸造,直到西元前九世纪才开始自行生产。[22]近年日本学者甲元真之从尕马台铜镜出发,提出星芒纹在中亚铜器及凌家滩玉器上的共通性,对过去铜镜起源的相关讨论提出质疑,并就殷墟出土铜镜之形制,认为与中亚所见不同,具有启发性。但认为殷墟为凸面镜、西周以后出现小型镜及凹面镜的线性发展说法则有待商榷。[23] (二)早期铜镜的类别、功能及定义问题 如O’Donoghue的怀疑,伴随铜镜起源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界定铜镜及其功能。学界在讨论被认为时代最早的尕马台铜镜时,便对其功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多就出土位置认为是胸前配饰。[24]对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的认定,则有胡博在讨论齐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连性时,径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圆形铜片残件称之为铜镜,使之成为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25]这些论述均反映了过去学界对早期铜镜的模糊认定。 这种模糊性所带来的问题,在出土大量圆形片状器物的青铜时代遗址中特别显著。A.A.提什金(A.A.Тишкин)及H.H.谢列金(H.H.Серегин)在讨论阿尔泰铜镜时,便指出考古学者在面对大量此类器物时,对于何者为泡何者为镜,有许多不同的意见。[26]阿尔泰南边的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及时代稍晚的甘青地区卡约文化墓葬也出土大量圆形铜牌饰,器类同样难以鉴别。[27]更显著的例子来自于西元前六到五世纪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墓地M。墓主人随葬三种型态的镜或镜形饰(图1)。[28]在综合相关出土资料,刘学堂以今日大兴安岭鄂伦春萨满巫师服装缀镜满身的形象为参照,提出凡于边缘有穿孔的圆牌,功能上应是悬挂于萨满巫师服装上的装饰或法器,而非实际用于照容。[29]这种说法得到许多学者支持,认为不论是天山北路或郑家洼子墓葬中所见的铜镜多与萨满信仰有关。[30] 图1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墓地M及出土镜类相关器物 1.M2.双钮镜3.镜形饰4.马头上的圆形器 (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年1期,图版1、5、6) 中原地区晚商及西周时期所见铜镜数量稀少,但界定问题同样困扰学者。依据镜面的弧度,过去研究论述中被称为铜镜的晚商及西周时期器物主要有平面、凸面及凹面等三种。对凹面镜是否可作为照容镜的怀疑,表现在不少研究论述中。如宋新潮认为阳燧与早期铜镜「仅仅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形式而已,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31]高西省对西周遗址出土的「凹面镜」有详细的论述,并罗列众多学者对个别「凹面镜」的称法及定义。综合分析后,提出与宋新潮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镜与燧「是使用性质根本不相同的两类器,是并存的,一照面饰容,一聚光取火。」因此提出「凹面镜」应正名为阳燧。[32]总体来说,学界虽北京白癜风治疗多少钱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比较见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anhuaz.com/xjebjd/2261.html
- 上一篇文章: 洪都拉斯一飞机降落时滑出跑道机身损毁严
- 下一篇文章: 四天五架飞机冲出跑道,揭秘背后的原因